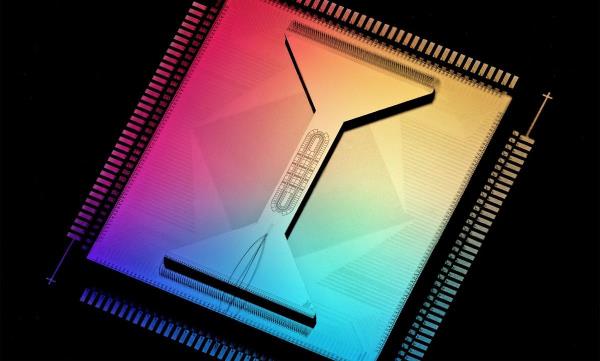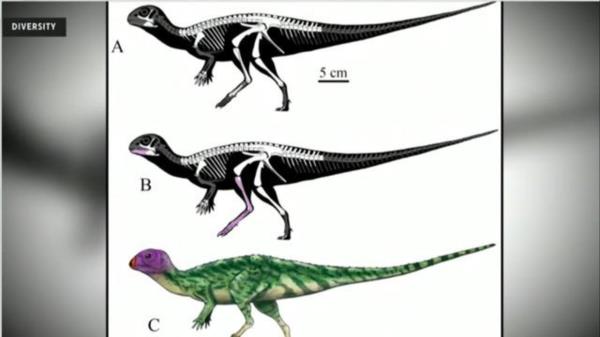我的兄弟,穆罕默德,在加沙近一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同时努力帮助那里的人民。他从一场摧毁了我们家的空袭的废墟中爬了出来,他目睹了我们太多的亲人受伤或死亡。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他还是安然无恙。然而,他最近因肝炎感染而病重。
穆罕默德是在加沙运作的一个较大的国际医疗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副主任。他与人道主义界密切合作,应对一场又一场灾难。但现在,脊髓灰质炎和肝炎等疾病开始在已经饱受摧残、虚弱、生病、疲惫、营养不良和绝望的人群中传播。加沙地带到处都是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和不卫生的条件;默罕默德在田间工作时无法避开它们。
疾病的蔓延、法律和秩序的崩溃、犯罪的激增、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加剧、保健系统的崩溃以及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流离失所的持续循环,已经彻底摧毁了加沙的人口。
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损失之后,加沙人民渴望一个没有哈马斯或以色列控制他们生活的未来。他们希望做出被迫做出的牺牲,以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然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从我哥哥的故事中,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巴勒斯坦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对人类的意义。去年10月,在哈马斯的凶残袭击导致以色列1200人死亡、数百名人质被捕一周后,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次空袭摧毁了我和我的大家庭在那里长大的四层住宅。我的兄弟、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奇迹般地从废墟中挤了出来,只受了轻伤。我家里的其他成员就没这么幸运了。
Ahmed Fouad Alkhatib:我从加沙听到的消息
那次空袭炸死了我12岁的表妹法拉(Farah),还严重伤害了她的双胞胎妹妹玛拉(Marah)和她的父母。此外,我父亲最小的弟弟易卜拉欣(Ibrahim)和利雅得(Riyad)也受了重伤。随后对加沙城埃尔-耶尔穆克(El-Yarmouk)社区的一系列空袭摧毁了一些幸存者曾在邻居那里寻求庇护的房屋。利雅得叔叔在那次袭击中丧生;他的尸体直到九天后才被找到,变成了糊状的人体组织。易卜拉欣叔叔的女儿伊斯拉被爆炸抛出大楼。她落在街上,被一块水泥板压住,全身瘫痪。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哥哥在加沙城的不同街区寻求庇护。他和他的家人忍受着轰炸,这些轰炸经常离他们的避难所很近,让人心跳停止。11月,他们到达了加沙地带的南部,那里当时被以色列军方指定为安全区。
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事们聚在一起,他们一起策划了一个恢复工作的计划,为人们提供医疗支持。他们开始收到成卡车的医疗用品和其他重要物品,并将其分发到加沙的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网络。
然而,在他抵达加沙南部的几周内,他面临着另一场悲剧。以色列空袭了我母亲的家,我在加沙的第二个家,造成29名家庭成员死亡,其他人严重受伤。房子里挤满了从加沙北部逃到南部寻求安全的人。当时,拉法的巴西社区处于一个相对安静的地区,远离任何活跃的战斗。《纽约时报》的利亚姆·斯塔克(Liam Stack)问以色列国防军,为什么我的家会成为袭击目标,鉴于妇女和儿童的巨大生命损失,这样的袭击怎么可能是合理的。以色列国防军只提供了一个关于哈马斯在民众中扎根的样板答复。
这次袭击杀死了我所有的姑姑和叔叔,以及他们的许多孩子——我的堂兄弟姐妹。年纪最大的死者是我的姨妈扎伊纳布(Zainab),她是一家之主,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当了几十年的老师。她以慷慨大方著称,总是把自己的空间、食物和资源提供给那些不幸的人。如果你曾经进过Zainab的家,你一定会吃得饱饱的;她会一个接一个地上菜,没有商量的余地,不理会任何让她停止热情上菜的请求。
然后是我的叔叔阿卜杜拉,他是一名医生,以经营拉法的主要医院和在第二次起义期间提供护理而闻名。他治疗了数千名被以色列炮火击中或在空袭或其他形式的轰炸中致残的病人。有时,他会和医护人员一起乘坐救护车,收集伤势最严重的人,希望能让病人稳定下来,直到进入手术室。有一次,一名青少年的心脏被以色列的子弹击穿,阿卜杜拉叔叔不顾一切地想给他止血,他把拇指伸进了那个洞里,救了那名青少年的命。他的努力受到了卫生部和公众的赞扬。
除了从事其他人道主义工作外,阿卜杜拉还在自家地下室开了一家诊所。这使他们家的房子成为社区的地标,人们在指路或打车时都会参考它。当他的孩子和我玩耍时,他会严厉地斥责我们。但当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包括我在他的诊所需要缝针的时候,他却给予了我同情。在我叔叔尤瑟夫去世后,阿卜杜拉承担起了家庭长老的角色,定期在家庭聚会上接待我母亲,并在她寡妇时特别照顾她。
空袭前两天,我哥哥还在家里,和扎伊纳布和阿卜杜拉一起吃午饭。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正在汗尤尼斯,他和家人一直在那里避难,他疯狂地跑回拉法。他花了三天时间寻找遗骸,其中许多都被烧焦了,很难辨认。我哥哥最终找到了扎伊纳布的遗体——她没有头,双腿完全被压碎,只能从她娇小的躯干辨认出来。太多的身份识别过程就像一个可怕而痛苦的人体拼图游戏,其中记忆的特征、形状和大小与人类遗骸相匹配。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拉法的家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那里。在加沙城拥挤的街道上,这是我逃离学校和生活的避难所。那是一个我们看电影、玩电子游戏、在大后院做项目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拉法的房子里遇到了亚西尔·阿拉法特、穆罕默德·达赫兰和其他巴勒斯坦高级政治人物。阿卜杜拉的大哥尤瑟夫叔叔曾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工作,领导巴勒斯坦特奥会。他自己也坐轮椅,因公正和独立而备受尊敬,经常受到其他政治和社会人物的访问。
拉法的房子就像一个迷你的联合国,在充满煽动性言论、煽动和对前进道路的激烈分歧的海洋中,它是某种安全港。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了解到巴勒斯坦事业的复杂现实。而这些也被空袭摧毁了。
这些是我家庭的故事,但加沙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这场战争不仅抹去了生命,也抹去了几代人的历史和记忆。纪念碑和历史地标被夷为平地;家庭文件和纪念品被焚毁;长者在他们的知识可以传递或记录之前就被杀害了。
Ahmed Fouad Alkhatib:以色列杀死了我的家人,但没有杀死我的希望
巴勒斯坦人民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日常苦难。尽管发生了激烈的暴力事件,特别是在第二次起义的高峰期和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但常态是低强度冲突。在巴勒斯坦的背景下,目前在加沙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战争必须是加沙的最后一场。该地区的领导人应该放弃对以色列的任何形式的武装或暴力抵抗,而是集中精力使加沙成为最好的自己。就以色列而言,他们必须真正放弃他们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他们的领海、领空和与邻国埃及的边界上行使真正的独立和主权,即使以色列的合法安全需求得到了考虑和解决。
我仍然相信这种转变是可以实现的。加沙面积小,人口密集,这使得实施务实的改革相对容易,这可以迅速稳定领土并结束苦难。尽管加沙目前处于困境,但它有机会成为巴勒斯坦有效自治的典范,展示一个没有占领的西岸会是什么样子。
加沙能够、应该、也必将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