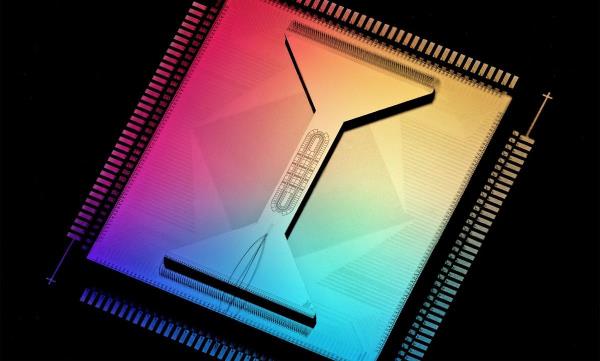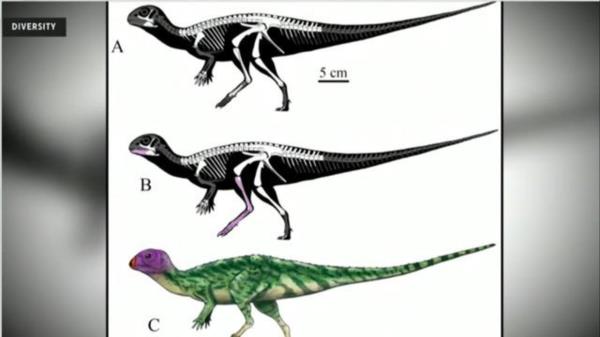1761年12月,英王乔治三世向美洲殖民地发出命令。在最近一次对传统的蔑视中,一些美国殖民地法官被任命为终身法官,与英国法官享有同样的任期。现在,国王打算明确表示,所有殖民地的法官只能“听命于国王”。
抗议浪潮席卷了殖民地。在北卡罗莱纳,反对这一决定的人一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前都拒绝接受这一命令。在新泽西州,州长不服从命令,立即被免职。在纽约,殖民地议会继续主张,殖民地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是终身任职的。纽约州代理州长卡德瓦拉德·科登(Cadwallader Colden)同情国王,但他对议会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演变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近乎精神错乱的愤怒”,最后他指责议员们试图“获得控制全人类思想的最广泛的权力”。四年后,一群暴民对不公平的税收——另一个专制统治的象征——感到愤怒,绞死了戈尔登州长的肖像,砸毁了他的马车,并把木片扔进了鲍灵格林的一个巨大的篝火里。

探索2024年10月号
看看本期的更多内容,找到你的下一个故事。
查看更多这些关于司法独立的强烈情绪从何而来?一些殖民者知道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或法国散文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关于权力分立理论的著作,该理论赋予政府不同部门相互制约和平衡的能力,防止任何部门积累过多的权力。但大多数人,可能包括在鲍灵格林焚烧州长戈尔登马车的暴民,想要独立法官的原因和他们想要革命的原因是一样的:对遥远、武断、非法的王权的本能怨恨。
这种本能一直伴随着他们。1776年,《独立宣言》指责国王“让法官的任期、薪水的数额和支付完全取决于他的意愿”。十年后,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在需要独立的联邦法官的问题上保持一致。
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认为,法官的薪水应该很高,以吸引“一流人才”。詹姆斯·麦迪逊担心,如果立法者可以随意提高或降低工资,那么法官可能会在做出不利于国会议员的裁决时犹豫不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将司法人员的工资与小麦“或其他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的价格挂钩。
最终,宪法的制定者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制度。为了保持法官的独立性,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但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国会议员制定司法人员的工资,不能减少。法官是终身任职的,所以他们不担心自己会因为某个特定的决定而被免职。他们可以因不当行为被国会弹劾,但这种情况很少见——自1789年以来,只有15名联邦法官被弹劾,其中只有5人是在1937年之前被弹劾的。
但在实践中,他们也受到规范和惯例的约束。例如,自20世纪初以来,国会就没有解散过法官不满意的联邦法院——这在更遥远的过去确实发生过。自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提议最多任命六名大法官,试图重塑最高法院,但以失败告终以来,法院精简的想法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自1957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派遣联邦军队前往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执行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以来,有权势的政客们大多同意尊重并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而那个时代的几位南方州长公然违反了这一惯例。(早些时候,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也曾违抗过这一命令。1832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裁定,与切罗基人签订的条约必须得到尊重。据说,杰克逊总统当时说,“让他来执行吧”;这句话是杜撰的,但杰克逊的情绪不是。)
我们法院的独立性正在瓦解,因为一些法官很乐意“为国王效劳”。最终,司法独立有一个更重要的保障:法官自身的品格。他们必须避免政治影响。他们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他们至少要尽量不听命于总统或州长。这可能是所有约定中最重要的。尽管对美国司法政治化的担忧可以追溯到共和国早期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尽管这种担忧在社会或政治变革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再次出现,但现代美国人普遍认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官将本着诚信行事。共和早期的政治哲学家,宪法的起草者,以及当今的法学院教授,大多都认为,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话来说,联邦法官将努力“将必要的正直与必要的知识结合起来”。
至少在最近,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些收入丰厚、不怕被解雇、没有任何财政、法律或政治压力的联邦法官,会试图以极端的党派方式修改法律,不仅是为了支持保守或进步的思想,而且是为了支持特定的政治家,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高法院最近就总统豁免权做出的一项裁决,似乎是为了帮助前(也可能是未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任命的地区法院法官违背了几十年的法律先例,保护第45任总统不受法律约束——这些都必须被认真对待,因为这表明我们法院的独立性正在崩溃,不是因为法官不受保护,而是因为一些法官很乐意“为国王效劳”。
在我进一步阐述之前,让我澄清一下,我不是法律学者,不是宪法历史学家,甚至不是美国历史学家。我之所以对司法独立的起源感兴趣,是因为2015年我住在波兰,我的丈夫参与了波兰的国家政治。(他是公民纲领党成员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政府的外交部长。)那一年,在同样合法的总统的合作下,一个由合法的、民主选举的议会多数组成的政府决定结束司法独立。出乎意料的是,这是非常容易的。
发动这场司法政变的政党被称为“法律与正义”(当时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它对宪法的攻击有几个因素。除其他事项外,执政党在议会通过立法,迫使年长的高等法院法官立即退休,这一举动最终赋予了法律和正义党任命大量新法官的能力(这与罗斯福计划解散美国最高法院没什么不同)。法律和正义的立法者创建了一个新的,违宪的机构,有权调查和制裁那些裁决令政府不满的法官。当宪法法庭(波兰相当于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政府的一项法律时,总理拒绝在官方法庭刊物上公布裁决。换句话说,她只是忽略了它。那就是:没有人可以强迫首相或执政党服从裁决。
其结果是对新规则下任命的法官合法性的困惑和司法党派之争的急剧上升。几年后,在华沙打官司的人通常会根据主审法官的类型而不是法律依据来评估自己胜诉的可能性。由法律与公正部非法任命的“新法官”,其裁决可能与根据过去25年来更为中立的制度任命的法官的裁决不同。
一些人对这种变化感到震惊。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那些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波兰生活过的老年人。Paulina Kieszkowska,自由法院(一个组织抗议,积极游说,并在欧盟法院提起诉讼反对所谓的司法改革的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最近告诉我,年长的抗议者记得“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法官的概念,完全是政治驱动的判决,英雄的人被判处死刑”,他们不想回到那个时代。Kieszkowska是一位波兰法官的孙女,这位法官因政治原因辞职。就像美国殖民者一样,她和她的同事们有生活在法治下的直接经验——这意味着法律是执政党、独裁者或君主所说的——与法治相反,当法律由忠于宪法的法院执行时,而不是由碰巧掌权的人执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我参加了第一批自发的支持司法独立的游行,令我震惊的是,参加游行的年轻人少之又少。一开始,司法政治化的威胁似乎并没有影响选举,也没有对民意调查产生太大影响。尽管由自由法院等团体领导的法律运动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欧盟法院发现波兰违反了欧洲法律——但事实是,司法机构的衰落对大多数波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论上的问题。权力分立是一个抽象概念,他们根本不担心。
最终,政治化的法院产生了对人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法律变化。2020年10月,宪法法庭(当时已经挤满了与法律和正义关系密切的高度党派法官)将波兰本已严格的堕胎法缩小到几乎完全禁止。在这一裁决之后,医生们开始拒绝给妇女堕胎,即使她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几名妇女死亡。
直到那时,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才有所反应。他们游行,他们组织起来,最终他们以异乎寻常的高人数投票,推翻了法律与正义政府。他们几乎太迟了。司法系统仍然是一团乱麻。数百名新法官仍在原地,他们的忠诚不明确,甚至可能是对自己的忠诚。他们只是中立地解释法律吗?还是说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表达任命他们的政党的意愿?波兰法院将因非法而受到玷污,并在未来几年受到怀疑。
在美国,即使是一个敬业、恶毒的总统和一个恶毒的国会,也很难复制波兰的经历。法官终身制被写入宪法。没有哪位总统可以轻易地一次撤换几十名法官,或者建立一个宪法外的机构来对他们施加控制。就连两党达成妥协也绝非易事: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提出了最高法院改革方案,包括可能的法官任期限制,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接受。但由于这可能需要宪法修正案,或者至少需要共和党的大力支持,这一姿态很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摘自2005年6月号: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任期太长了
但波兰经历的一个因素可能是相关的:规范和惯例的变化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失方向的深度。想想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或几年里看到或学到的东西。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正在接受可能对他们的法理学有兴趣的人赠送的数额巨大、未公开的礼物;其中一名法官的妻子在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不止一位大法官在确认听证会上误导国会,谎称他们有意推翻罗伊诉韦德案;金钱和说客在最高法院的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打破惯例,阻止了一项提名,然后又批准了另一项提名;现在,共和党主导的最高法院已经将豁免权扩大到一位违反法律的共和党前总统身上——所有这些都产生了累积和破坏性的影响。在两极分化的两派看来,最高法院和所有其他联邦法院现在都显得更弱、更政治化、更容易操纵、更不受宪法约束。盖洛普(Gallup)今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5%的民主党人和66%的共和党人仍然支持最高法院,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总体而言,对法院的尊重处于历史低点。
艾琳·坎农的特殊案例可能是一个先兆。佛罗里达州南区的坎农法官(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说法)最低限度的资格,做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在法律上有问题的决定,这些决定似乎是故意设计来帮助任命她的总统特朗普逃避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7月中旬,她驳回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对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扣押敏感国家安全文件并向联邦调查局撒谎的指控,这违反了《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主流法律学者认为坎农的裁决基于高度可疑的理由:史密斯一开始就不应该被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任命,而且史密斯在行使他“不合法拥有”的权力。
摘自2020年7 / 8月刊:安妮·阿普勒鲍姆谈共和党领导人为何继续支持特朗普
在这一决定之后,Joëlle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法律学者安妮·莫雷诺(Anne Moreno)告诉《纽约时报》,坎农“单枪匹马地颠覆了三十年来以两党方式公平使用的既定法律”。美国杰出的宪法学者之一劳伦斯·特拉布(Laurence Tribe)写道,坎农的决定相当于“向法治投掷了一把大锤”。坎农之前的裁决已经为她赢得了来自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严厉而不同寻常的指责,她的两位经验更丰富的同事——包括共和党任命的南区法院首席法官——建议她放弃特朗普的案子。
现在想象一下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在此期间,又有几十个艾琳·加农斯(Aileen Cannons)被任命为法院法官——几十个资历最低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捍卫总统或为他的敌人报仇,而不是捍卫法治。再想象一下,2028年当选的另一位总统是民主党人,他觉得没有义务遵守这些高度党派化的法院做出的决定。或者想象一下,在2028年的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中,副总统j·d·万斯(J. D. Vance)支持试图阻止合法权力移交的叛乱分子,就像他说过的那样,他会在2020年这样做——当时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法律顾问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数十项主张。如果在2028年和2029年,法院做出相反的裁决,意图帮助扶植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总统,那会怎么样?
听着:民主的终结已经开始了
这些都是想象力的小小飞跃——事实上,它们根本算不上飞跃。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十年前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位受到多项指控的叛乱前总统现在领导着共和党的竞选,而大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对这种威胁漠不关心。革命时代的殖民者被国王统治,决心不再重蹈覆辙,一些波兰人记得共产主义的正义,因此为阻止它的回归而斗争。今天的美国人没有经历过联邦司法机构的裁决是基于对特定政治家或政党的忠诚。也许这让我们陷入了一种“这里不可能发生”的安慰。但正如特里布所说,我们面临的真正可能是“一个帝国式的司法机构与一个帝国式的行政机构携手同行”: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使美国免受独裁统治影响的法律和规范会慢慢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