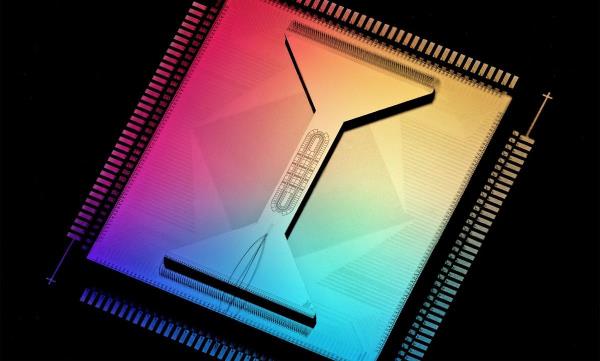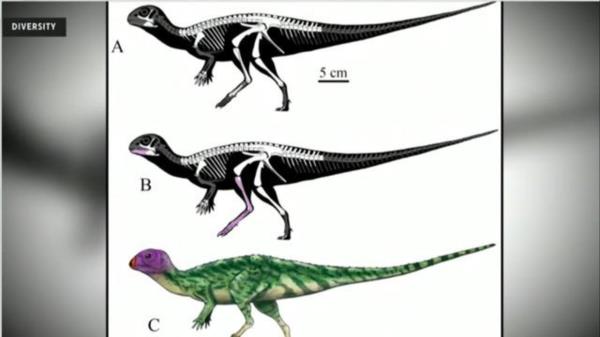预测战争永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即使是最傲慢的专家或政治家,也很快学会在他们的预测中加上一句“你永远无法预知”。但考虑到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政府、评论员和领导人不仅不善于判断战争可能走向何方,而且不善于判断战争如何发展,这一点令人震惊。
1990年,许多受人尊敬的分析人士和记者预测,在科威特和伊拉克沙漠中,久经沙场的伊拉克军队面对寡不敌众、被认为软弱无力的美国军队时,会发生一场血战,随后会陷入泥潭。然而,海湾战争以一场迅速的冲突告终,友军的炮火和意外事故给美军造成的损失与敌军的火力一样大。伊拉克人在武器上、战术上、领导上都处于劣势,而且——正如我们后来了解到的——实际上在数量上超过了与他们对抗的部队。
Garrett M. Graff: 911之后,美国几乎把所有事情都搞错了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规划者同样高估了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的党羽压制了德国师的数量,这在历史上是错误的,这让国防规划者和评论员相信,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轻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干预波斯尼亚将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战斗。它不是。
从那以后,双方的错误估计一直在继续。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四年里,美国一直在挣扎,让自己相信,它只是在与数量日益减少的“前政权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人”进行非常规战争,这些人可以被摇摇欲坠的伊拉克新军队处理掉。这需要一个更现实的观点——以及战争中最好的指挥官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来改变评估和战略。
如果说在2007年之前,过度乐观曾困扰着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策,那么对于扭转局势的可能性,国会中弥漫着持久而同样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事实上,就在彼得雷乌斯和他的五个新旅扭转局势的时候,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新参议员和一位来自特拉华州的资深参议员——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总统——都确信伊拉克战争毫无希望。再次回到过度乐观的话题:21世纪初,美国政府错误地判断了塔利班对我们的阿富汗盟友发动战争的速度和程度;2021年,当我们宣布最终撤军时,他们对阿富汗政权的崩溃感到震惊。同样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10年前,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再次爆发。
著名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自信地预测,俄罗斯将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闪电战。然而,远在西方援助的全部分量在乌克兰得到体现之前,入侵者的能力就被证明远不如任何人预期的那么强,而防御者的效率则远比任何人预期的要高。现在,类似的模式正在发生,匿名的军事泄密者和所谓的专家表示,乌克兰的反攻失败了,因为战斗机没有像1944年乔治s巴顿(George S. Patton)和第三集团军(Third Army)从诺曼底滩头突进时那样进行机动。
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毕竟,无法预测一场战争的实际进程,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派都是一种现象,在职军官和情报官员与记者和评论员一样普遍。
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因情况而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错误判断部分反映了克服军队在越战后对镇压叛乱自我强加的失忆的困难。“我们再也不会那样做了”的情绪导致美国陆军停止考虑反叛乱。2004年,当我为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领导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时,我发现手头上的平叛手册是越南时期的,假设是一支由戴着草帽、穿着黑色睡衣的共产党灌输的农民组成的反对派军队。
对乌克兰的错误判断有不同的原因:对武器和装备数量的狭隘关注,对军事理论与实际执行能力的混淆,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怀疑,即如果你与美国结盟,你可能是腐败、无能和懦弱的。这对越南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注定要失败,但对乌克兰来说却是大错特错。由于对俄罗斯熊有一种崇敬的分析亚文化,一些人很难接受这只熊患有风湿病、近视、长了疥疮、爪子残缺不全。
很少有人研究战争。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大学里充斥着“安全研究”的课程,这意味着,在实践中,诸如军备控制、威慑理论和威胁下的谈判等内容。今天的记者、学者和官员都是在那里接受教育的。曾经拥有杰出军事历史学家的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的麦克·科夫曼、普渡大学的冈瑟·罗森伯格、斯坦福大学的戈登·克雷格、杜克大学的西奥多·罗普——看到他们被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所取代,这些学者不太直接关心(或者根本不参与)当国家召集军队、舰队和空军进行最后的国王辩论时发生了什么。
对于平民来说,结束征兵意味着他们不再熟悉军队的运作原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不再熟悉军队的愚蠢和低效。随着政治、学术和新闻领域的军事经验逐渐枯竭,专业军官只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作战:无论永远的战争看起来多么残酷和致命,美国总是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包括在空中和太空的优势,以及安全的后勤基地和通信线路。这些冲突是艰难的,往往是痛苦的经历,但它们不是那种每天杀死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战争,也不是针对那些可以在空中或海上挑战我们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战争。这种情况自1945年以来从未发生过。
我们的高等军事教育制度只能部分地弥补这种直接经验的缺乏。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担任国防部长时曾呼吁“让战争回到战争学院”。但是,除了在师资和课程方面有重要和值得尊敬的例外,战争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将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军官带入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国防决策和分析的政治军事世界。这些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精英战争策划者和战争学者的温床。
许多人仍然坚信,无论如何,真正的战争不会再降临到我们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军方领导人知道弹药库存太低,他们也不会敲打文职上级的办公桌,恳求他们增加弹药储备。正因为如此,政治领袖们没有对美国人民坦诚,如果我们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防止乌克兰遭遇的恐怖,我们就需要在国防上投入更多——多得多的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些有价值的武器——特别是地雷和集束弹药——的人道主义限制能够成为法律或政策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何故认为这些恐怖永远不会成为必需品。
大卫·弗拉姆:重新考虑伊拉克战争
我想到了两种解药。第一种是更多的军事历史——老式的枪炮和号角之类的东西,对当代学术思想来说,这是过时和尴尬的。20世纪最伟大的说英语的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曾经说过,人们应该从广度和深度上阅读军事史。一个人应该对很多战争有所了解,对少数战争也要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培养一种直觉,知道战争中哪些事情会顺利,哪些会糟糕,什么是可以预料的,什么是不能预料的。
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诚实的会计。军事判断的错误——甚至是大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错误判断发生时,做出错误判断的人应该问自己一些痛苦而深刻的问题。(我写《大棒》的第二章是为了纠正我自己对伊拉克的错误判断。)当这样的错误真的非常严重、持续存在,而且更糟糕的是,没有得到承认和检验时,记者、专家和官员应该考虑,是否应该像今天的乌克兰战争一样,把那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放在快速拨号上。否则,最近的错误集肯定不是最后的,甚至不是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