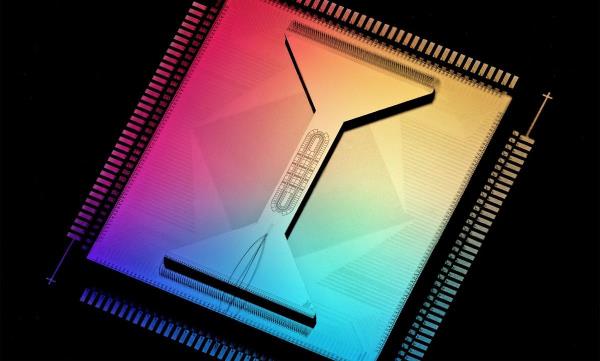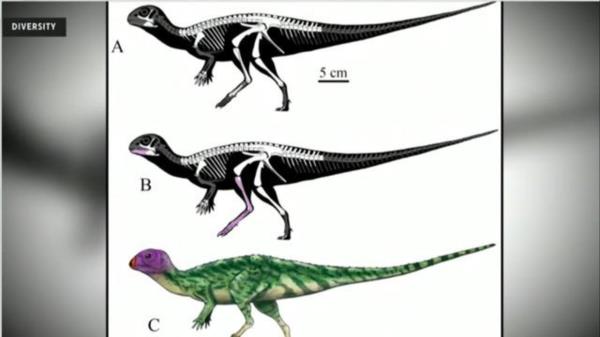1953年6月,在麦卡锡时代的鼎盛时期,当国会调查人员和私人团体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追捕“颠覆性”或仅仅是“令人反感”的书籍和作者时,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协会图书出版商理事会发表了一份名为“阅读自由”的宣言。这份文件捍卫了言论自由,谴责了审查制度和语言的一致性,其清晰和力量在今天令人吃惊。它主张“观点和表达的最广泛多样性”,反对根据“作者的个人历史或政治派别”来清洗作品。它敦促出版商和图书馆员抵制政府和私人的压制,并“通过提供丰富思想质量和多样性的书籍,赋予阅读自由充分的意义”。这份宣言不仅针对官方审查制度,还针对更广泛的高压氛围和群体思维。报告的结论是:“我们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人们读的东西不重要,从而提出了这些命题。我们相信人们所读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想法可能是危险的;但是压制思想对民主社会是致命的。自由本身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但它是我们的。”
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了“阅读的自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在同月敦促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毕业生不要“加入焚书者的行列”,他给宣言的作者写了一封赞扬信。在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份宣言给了图书馆员和出版商坚持原则的勇气。一位图书管理员后来写道:“那里发展了一种战斗职业,由敬业的人组成,他们确定自己的方向。”
今年6月,在《阅读的自由》出版70周年之际,图书馆和出版商协会重新发行了这本书。许多出版商、图书馆、文学团体、公民自由组织和作家都签署了支持其原则的协议。然而,许多机构签署者——包括“五大”出版集团——经常违反其主张,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这样做。在当时,当审讯官正在毁掉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的时候,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能像他那样毫无歉意地捍卫知识自由。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2023年的美国文学界不像1953年的美国作家那样能够坚持“阅读自由”的原则。
今天对知识自由的攻击来自几个方面。首先,也可能是签署人最关心的,是由州长、州立法机构、地方政府和学校董事会发起的一场官方运动,以淘汰他们不喜欢的书籍和思想。大多数目标在政治上属于左派;大多数内容所呈现的事实或表达的关于种族、性别和性的观点被审查者认为是危险的、分裂的、淫秽的或完全错误的。这项行动早在2020年就在德克萨斯州开始了,之后公众的歇斯底里和政治机会主义将运动蔓延到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州,并蔓延到各个教育水平,从图书馆书架和课堂阅读清单上撤下了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等作家的数千本书。
鉴于各州和学区有责任制定公立学校的课程,并非所有这些都能被称为政府审查。但是,阻止学生接触有争议的、不受欢迎的、甚至冒犯性的作家和思想的法律和政策,相当于一场强有力的禁书运动,其中一些可能违宪。这场运动源于美国的一种传统,即对快速变化和非正统思想的狭隘恐慌。你可以把田纳西州1925年的scope审判和佛罗里达州2022年的Stop WOKE法案划清界限。这种对知识自由的威胁,是在图书界占主导地位的进步和开明人士最容易反对的威胁。在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或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 Foundation),没有人会犹豫为《性别酷儿》和《使女的故事》发声。
雷·布拉德伯里曾经说过:“烧掉一本书的方法不止一种。”“世界上到处都是拿着点燃的火柴跑来跑去的人。”对知识自由的第二个威胁来自另一个来源——来自家庭内部。这种威胁是美国笔会刚刚发表的一份新报告的主题,“书鞭:文学自由、网络愤怒和伤害语言”。(因为我过去写过关于审查制度和语言的文章,国际笔会让我阅读并回复了早期的草稿,并给了我一份最终版本的预印本。)该报告关注的是最近出版商和作者在网上组织的压力下取消自己的书的模式,有时是在出版之后,或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员工(通常是年轻的员工)的压力下。自2016年以来,国际笔会追踪了31起可能被称为文学杀婴的案件;其中一半发生在过去两年。报告指出:“这些书都没有因为虚假信息、美化暴力或抄袭的指控而被撤回。”“他们的内容或作者只是被视为冒犯。”
有几个案子成了大新闻。在员工罢工后,阿歇特出版社取消了伍迪·艾伦的自传,布莱克·贝利的菲利普·罗斯传记在诺顿出版社出版后被撤回,这两本书的作者都被指控性行为不端(艾伦和贝利否认了这些指控)。出版商会在作者发表公开言论后取消出版,比如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英国记者朱莉·伯奇尔和右翼煽动者米洛·扬诺普洛斯。
在一个特别疯狂的案例中,一位名叫娜塔莎·泰恩斯(Natasha Tynes)的作家即将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一部犯罪惊悚小说,她看到华盛顿特区地铁系统的一名黑人员工在火车上吃东西(这违反了地铁系统的规定)。她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该女子在交通管理局的照片,并提出了投诉,很快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病毒式传播的种族主义者。几个小时后,她的发行商珍禽图书公司(Rare Bird Books)就放弃了这本小说,并在twitter上说,泰恩斯“今天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版商加州冷血出版社(California Coldblood)在试图与这本书撇清关系后,最终“出于合同义务”继续出版了这本书,但这本小说已经死了。“你怎么能指望作家是完美无缺的人呢?”泰恩斯向笔会哀叹道。大多数出版商现在都在图书合同中加入了一个样板道德条款,使这些取消合法化——这是一个与那些出版商所支持的“阅读自由”原则相矛盾的漏洞。
报告中讨论的许多案例与作者的冒犯性言论或不良行为无关。相反,它们涉及措辞、人物塑造、情节、主题或作者身份等方面的错误。去年,Picador公司放弃了一位教师的获奖回忆录,原因是该书被指责对种族不敏感。在批评家指出作者是白人后,Wipf和Stock撤回了一项关于黑人女权主义文化的学术研究。因为希特勒的缘故,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先发制人地封杀了一本希特勒子女的传记。四本青少年和儿童小说(似乎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因被认为有冒犯性的故事和描述而被撤下。其中一本名为《狼的地方》(A Place for wolves)的小说讲述的是科索沃与塞尔维亚战争期间,两个美国同性恋男孩在科索沃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科索科·杰克逊(Kosoko Jackson)本人是一名文学犯罪检察官,他在Twitter上指责他违反了自己关于身份的规定,对合适的题材有严格的限制:“关于民权运动的故事应该由黑人写,”他在Twitter上写道。“争取选举权的故事应该由女性来写。因此,关于男孩在可怕和改变生活的时代的故事,比如艾滋病的流行,应该由男同性恋者来写。为什么这么难得到这个?”
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是身份——或者,用报告中多次使用的一个短语来说,“边缘化的身份”。“有害的”语言、“表现”的失败、“挪用”或一般意义上的“有问题的”内容——这些可能会毁掉作家作品的“绊线”都与身份有关。2020年,白人作家珍妮·康明斯(Jeanine Cummins)的小说《美国内幕》(American Dirt)获得了大量关注(据报道,她的出书合同达到了七位数),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墨西哥母亲和孩子逃离贩毒团伙的故事。有人谴责她抓住了一个本应属于拉丁裔作家的机会,一些评论家说,这个作家本可以写出更好的书。她的出版商Flatiron/Macmillan没有撤下这本小说——因为它卖得太多了——但它以安全考虑为由取消了康明斯的巡回演出,并发表了一份自怜自怜的声明。《美国丑闻》的磨难向出版商表明,跨越身份界限可能是危险的,这促使一位接受笔会匿名采访的前编辑问道:“我们是在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写任何故事吗?”你一定要有某种身份吗?人们对此有很多担忧。”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每年出版的数万本书中,只有几十个尴尬的决定和小争议有什么大不了的。答案是,这些事件揭示了一种从众和恐惧的氛围,这种氛围破坏了图书出版必须不仅仅是一项业务的任何主张。报告中描述的大多数被取消的书籍都是普遍存在的正统观念的受害者。在最严格的情况下,这种正统将身份的要求置于其他一切之上——文学品质、作者独立性、阅读自由。它的影响可以从许多被取消的书籍已经做出了明显的努力(尽管有些笨拙)来遵守公平和包容的价值观中看出;娜塔莎·泰恩斯(Natasha Tynes)试图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少数族裔作家”,免受网络攻击。
最终,正统使压制书籍变得没有必要,因为它导致编辑和作家进行自我审查。笔会采访的一位被取消的作者说:“这让我在创作上失去了动力。总有一个审查员站在我的肩膀上,告诉我不能写这个或那个话题。”哪个作家能诚实地说他们不是这样的?接受笔会报告采访的编辑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具名。如果不是担心作者的命运,他们还害怕什么呢?
水线以下是所有没有签约的书,甚至没有写,因为这些例子被公开了。畅销书作家理查德·诺斯·帕特森(Richard North Patterson)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他的最新小说被“大约20家”纽约出版商拒绝了。这部小说讲述了一段种族间的关系,以反对投票权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帕特森写道:“似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只有那些亲身遭受歧视的人才可以安全地通过虚构的角色来描绘歧视。”(《审判》于6月由田纳西州一家保守的基督教公司出版,目前在亚马逊所有书籍中排名约3.7万。美国笔会报告中的几本书被大出版商取消了,被影响力小得多的小出版社抢去了。)
笔会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组织。在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和许多声明谴责州和地方政府的禁书之后,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它不能忽视一种更接近国内的压制模式,即出版笔会成员并赞助其筹款晚会的组织。
今年5月,两名乌克兰军人作家宣布,如果两名俄罗斯作家也被列入另一个小组,他们将退出该组织的世界之声节,笔会陷入了自己的言论自由争议之中。笔会没有取消已经抵达美国的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回战场,而是要求俄罗斯作家和小组的主持人、笔会董事会成员玛莎·格森(Masha Gessen)站在另一个旗帜下发言,那就是美国笔会。相反,俄罗斯人和格森决定取消他们自己的活动,格森从董事会辞职,以抗议被视为国际笔会屈服于乌克兰人的要求。(其中一名俄罗斯作家后来说,如果乌克兰人不希望她参加,她就不想参加。)一个月后,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暂停出版她的下一部小说,因为乌克兰读者对小说以苏联为背景感到不安,笔会宣布这是“令人遗憾的”和“顽固的”。所有这些都只是表明,当你不是那个面临不愉快后果的人时,你更容易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
国际笔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和内部辩论这份新报告,预计会引起争议。早期的草稿受到了反射性的回避和战术批评的阻碍,其中一些仍然存在于已发表的报告中:对文学危害的指控“可能会落入使用相同修辞的右翼书籍横幅的手中”;《美国丑闻》的出版商如果在推销这本小说时更敏感一些,或许就能避免麻烦。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份报告是一份重要的、甚至是勇敢的文件。面对不断的愤怒,美国笔会正在为一个似乎已经失去勇气、忘记了使命的图书行业提供指导和支柱。在它的建议中,报告敦促“出版社应该很少,如果有的话,从流通中撤回书籍。”它呼吁在任何有关取消的决定中提高透明度和作者的参与。在线评论网站Goodreads被要求“鼓励真实的评论”,防止“评论轰炸”。在Goodreads上,暴民有时会在书还没完成之前就把书打死,更不用说出版和阅读了。
这些技术上的修正将极大地改善出版行业的政策和程序,但它们无法解决更大的问题——一种扼杀图书界的不宽容和怯懦的氛围。在报告的结论中,笔会呼吁“在文学话语中进行更广泛的语气转变”,这是必要的,但可能超出了任何报告的力量。从本质上讲,PEN是在对剩下的守门人说:“记住你的目的”,对新来的不速之客说:“不要用言语限制言语。”为了获得灵感,它全文转载了《阅读的自由》,并敦促图书界的工作者将其铭记于心。美国笔会主席阿亚德·阿赫塔尔(Ayad Akhtar)告诉我,他希望出版商在为新员工提供DEI培训的同时,将这份70年前的宣言纳入其中。国际笔会希望它的报告能产生类似于之前那份文件的效果——让出版业再次成为“一种战斗的职业”。
然而,有些东西阻碍了报告使用“阅读自由”的大声语言。我认为困难在于国际笔会去年发表的一份较早的报告。
在《字里行间的阅读:种族、平等和图书出版》一书中,笔会详细研究了美国图书行业一直以来的情况,尽管最近有所改善,但它仍然是一个由白人、关系良好的富人组成的俱乐部世界。它展示了一幅有数据支持的可怕画面,即“作家、编辑和出版商策划美国文学的白色镜头”。它呼吁出版商雇佣和提升更多有色人种的工作人员,出版更多有色人种作家的书,给他们更高的预付款,更聪明、更有力地销售他们的书。
这两份报告相互关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第一次表明,整个行业需要加强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运动。第二种观点主张更大的自由,以挑战文学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的限制。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
笔会可不这么认为。这份新报告指出:“文学界必须制定一条促进多样性和平等的道路,而不是让这些价值观成为针对某些被认为在这些方面不达标的书籍或作家的棍棒。”用国际笔会执行董事苏珊娜·诺塞尔(Suzanne Nossel)的话来说,“你可以为一些人拆除出版的障碍,而不必为另一些人重新设置障碍。”但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仅因为实际的限制,多少书可以可行的出版。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完全有可能在不制造审查气氛的情况下扩大机会。在我们的世界里,DEI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将社会正义置于出版中心的努力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于“代表性”和“危害”的争议,从而导致了禁书。第一份报告将DEI作为一项紧迫的道德事业发表。第二份报告对“员工越来越期望出版商在管理目录和作者名单时承担道德立场”提出了质疑。但这些员工无疑认为,他们正在实现第一份报告的愿景。
社会公正和知识自由并不是天生对立的——往往是相互依存的——但它们也不是一回事。《阅读自由》说得很清楚:“(出版商和图书馆员)建立自己的政治、道德或审美观点作为决定什么应该出版或传播的标准,将与公众利益相冲突。”这一声明是在知识自由事业是非意识形态的,甚至是反意识形态的时候写的。它的作者提倡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广泛和最高质量的观点表达。但是,在笔会的新报告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努力,即调和其早期报告的思想,在早期报告中,每一个计算都归结为身份,以及对创作文学所必需的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思想的辨别性判断和开放性。正如一位编辑告诉我的,“人才是不公平的。”
去年,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美国最大的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对第三大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的收购(收购实际上会使这家企业集团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今年,整个行业的图书销量下降,带来了裁员浪潮;上个月,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的高级编辑在解雇的阴影下被给予了买断的选择,出版界一些最杰出的看门人也离开了。这些事件让我想到了对书面文字的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攻击。
这一点比禁书和取消图书更隐蔽、更普遍,因此更难看清,更不用说反对了。这是每个作家和读者都能呼吸到的空气:出版业正在整合成一个近乎垄断的行业;异端与冒险的相应萎缩;员工经济状况脆弱;书店和书评的衰落;公众的文盲率越来越高;不顾政治压力,学校英语教学的减少;数据处理将创意转化为机器制造的产品,将媒体转化为高度敏感的人气晴雨表(人工智能即将取代人类独创性的最后痕迹)。所有这些趋势都是对自由智力的攻击,不是由“自由妈妈”或YA Twitter发起的,而是由马克·扎克伯格、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和亚马逊发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攻击是前两种攻击的基础,因为通过算法,强烈的情感和极端的语言被编入了各种类型的图书横幅的大脑,这些算法使少数科技和媒体巨头受益。
文学和新闻从来都不是赚钱的领域。但与30年前相比,如今找到一份严肃而持久的职业的机会要小得多。我不禁想到,这些情况与出版商愿意被几百条推文吓到有关。也许多年的整合和不稳定已经削弱了他们对图书出版使命的信念,以至于网上和内部的一点愤怒就足以抹去这种信念。如果编辑的功能是匹配作者和主题的身份,然后收集数据来衡量产品的成功,也许看门人最终失去了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