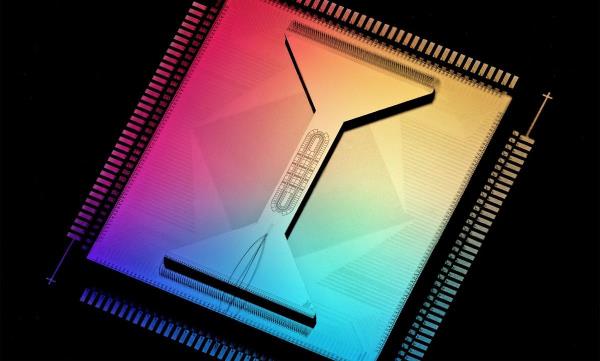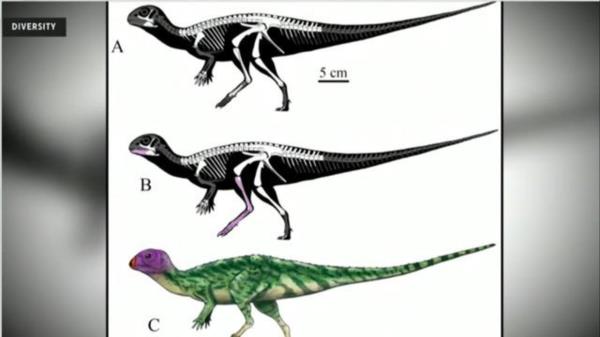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为我种了一棵树——一棵螺旋柳——在一条小溪旁,这条小溪穿过我们位于纽约伊萨卡的家的院子。那棵树,曾经是一棵树苗,长到了30英尺高。我记得我8岁时爬上树干,然后从细长的树枝上滑下来,试图避免掉进岩石流。后来,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目睹了这棵树和小溪之间的一场缓慢的消耗战,河床侵蚀着螺旋柳扎根的河岸。
记忆是善变的。它定义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认为自己是谁。它帮助我们在不连贯的生活中创造连贯的故事。然后我们的记忆就消失了。我还保留着关于童年和母亲的其他痛苦回忆。但随着她变老,我也变老,我意识到有些记忆需要被压榨,就像橙子一样,直到只剩下爱。
去年夏天,我从佛蒙特州的家开车去伊萨卡的退休社区看望我的父母。他们俩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但最近搬到了不同的房间。他们都患有痴呆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说过话。我有一年没见过他们了,我也不是很期待。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92岁的母亲逐渐失去了大部分记忆。一开始,她的痴呆症有一个好处。比如,她变得不那么焦虑了,对我坐飞机的事也不那么沮丧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再想起2015年大儿子去世的事。最终,她变成了一个兼职的幻想家,天真地编造一个从未发生过的过去——比如她从康奈尔大学毕业。
那个夏末的下午,当我在记忆护理中心的自助餐厅找到她时,她正在独自用餐。在那个阶段,她每天睡20多个小时,所以我很幸运地发现她醒着。出乎意料的是,她的棕色头发笔直地竖起来,就像一个卡通人物把手指插进了电源插座里。她的表情显得很紧张,几乎是扭曲的。在养老院的早些年,她曾同情过那些住在记忆护理中心的人。
当我坐下时,妈妈问我从哪里来,听说从佛蒙特州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她对我走了这么远感到惊讶。
“你住在这里的哪个街区?”她问。“奥瓦斯科,卡尤加,还是塞内加?”
我恍然大悟,她以为我是别人。我母亲和我聊天,好像我60岁了,还在做教授,是一个退休人员。
像拳击手一样,我开始调整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讨论。我们共同的过去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她今天过得很不顺,我也是。
杰弗里·洛夫:在不想生和不想死之间
在与餐厅工作人员拉锯战的同时,我妈妈多次喊她的甜点,一碗香草冰淇淋。一位看护者试图哄她多吃一些煎蛋卷。我母亲开始坚持要吃甜点。几轮之后,他们同意让她再吃一口鸡蛋。当服务员转过身去时,她把食物吐回她的盘子里。“冰淇淋!”自助餐厅里再次响起。
突然,我妈妈转向我,脱口而出:“你的父母在哪里?”
我没有回答。这是一个人可能会问孩子的问题——一个迷路的孩子,一个父母失踪的孩子。
我妈妈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回荡在我们童年的家里。那件事的记忆至今使我不寒而栗。她威胁说:“等着你爸爸回来!导致我父亲甚至不知道原因的鞭打。用皮带或其他东西鞭打我们只是他父亲的职责之一。
1962年秋天的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卡尤加湖南端的斯图尔特公园。他8岁,我7个月大。当初秋的落叶飘落时,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婴儿车里,呼呼大睡。母亲告诉弟弟她要去办点事——这是去趟女洗手间的暗号——并吩咐他盯着我。
等她走远了,他就溜掉了,爬上了一棵垂柳。妈妈回来的时候,马车和我都不见了。
在疯狂地抢了一毛钱后,她从附近的公用电话里打电话给警察。没有人责怪我弟弟,因为他只有8岁。没有人责怪我妈妈不带孩子。绑架在伊萨卡岛很少见,而且那是另一个时代。
几个小时后,警察发现一位老妇人推着我的婴儿车。很显然,警察告诉我的父母,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对我也没有更大的期望,只是想让我在公园里散步。指控没有被提起。
当时我还太小,自己不记得这件事,但多年来,“斯图尔特公园的蹦蹦跳跳”被我的家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在餐桌上,或者当我们中的一个人在杂货店离我妈妈走得太远的时候。渐渐地,这个故事有了记忆的黏性。
我现在对那个秋天的日子有着生动的,似乎是第一手的印象。作为一个玩笑,我的哥哥们美化了这个故事,声称那位女士把我和另一个婴儿交换了。这种转变对我很有效,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异类。
去年我在同一趟旅行中拜访了我父亲。他想起了我的名字,但我们的交流围绕着一个问题——“你住在哪里?”——提出并回答了很多次。他问得真好。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与他结婚68年的妻子即将步入人生的最后阶段。
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
她的那碗冰淇淋一端上来,妈妈就没理我,把它捡起来,走回走廊对面她的房间,随手把门关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着她走进房间,墙上挂着我们小时候她亲手做的七只圣诞袜。
她只吃了几勺冰淇淋,把盘子放在她的边桌上,然后爬上床,穿得整整齐齐。她惊愕地看着我,说她要睡觉了。我走过去和她吻别,但当我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时,她对卧室里的陌生人显得很警惕。我不想再让我们俩感到不安,就退了回去。
我也开始健忘了。时间不在我这边。故事在我有机会分享之前就悄悄溜走了。家人和朋友比我更清楚地记得我与工作有关的旅行,甚至我过去的恋情。我把事情记下来:“买牛奶”;"向神经科医生申请认知评估"我已经活过了我的螺旋柳。四十多岁的时候,这棵树倒下了,因为脚下的土地屈服于流动的溪流。我是我母亲的儿子。
在我去伊萨卡旅行几个月后,我妈妈中风了。她被直升机送往医院,在那里她接受了手术,以消除脑部的血块。
在我去那里的时候,我的妈妈裹着一件斑驳的灰绿色病号服,睡不着。但她的监测仪很安静,没有哔哔声,气氛也很平静。我静静地坐着读《堂吉诃德》——“没有时间抹不掉的记忆。”
很快,情况变得很清楚,我妈妈不会康复了。她说话和吞咽都有困难。必须安装一个永久性的喂食管。在她这个年纪,物理治疗很有挑战性。她签署了一份“不进行复苏”的命令,由于她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我和我的兄弟们决定寻求临终关怀。她回到了养老院。从那以后,她只吃冰片。
我妈妈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醒着的时候也有清醒的时候。一天早上,她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特别警觉。她说不出话来,但她的眼神表明她认出了我和和我在一起的哥哥。我们摘下了面具,这样她能更容易地看到我们。在下面,我戴着一个新冠风格的椒盐胡子,它的新鲜感照亮了她的脸。
“我忘了怎么刮胡子,”我告诉她。
妈妈笑了。就像一个喜剧演员和他的观众交流一样,我觉得她很快就明白了——母子关系仍然存在。在杂乱的管子和电线中,我找到了她的手。
几天后,我的一个兄弟给她看了一张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一家的照相照——五个男孩和我们的父亲穿着灯芯绒西装,她穿着她最好的裙子,戴着一个胸花——她抓住胸花按在胸前,说:“这就是他们所有的人!”
她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你的父母在哪里?”她就在那儿。我就在那儿。
随着我妈妈的健康状况下降,她的疼痛通过药物缓解,她变得没有反应。在她弥留之际,我的哥哥为她演奏了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boh<e:1>》,由她最喜欢的歌手卢西亚诺·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主演。我们起草了她的讣告。
当我妈妈还住在临终关怀医院时,我去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假期,去意大利看望我的好朋友。在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后,我们回到了米兰。当我们围坐在他们的餐桌旁时,我哥哥发短信说:“刚接到电话。妈妈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去世了。”
我哭了。我认识了41年的意大利朋友们,他们想安慰我,却又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和她在一起。对于以家庭为中心的意大利人来说,我触犯了一个禁忌。我们默默地盯着牛膝。
我应该为谁采取不同的行动?给我妈妈?给我吗?为你?
在我忘记自己的过去之前,我会记住这些。我找不到我妈妈。从她的笑声中,从我们一起的笑声中,我知道妈妈爱我,我知道她知道我爱她,也许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