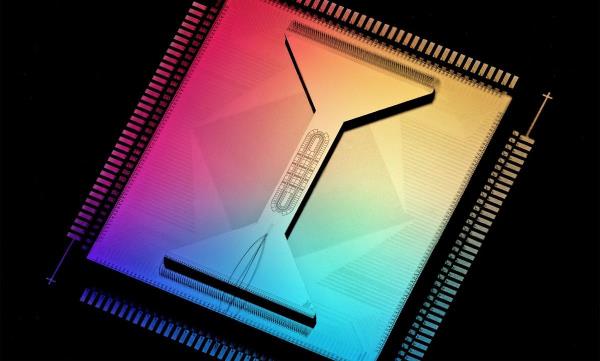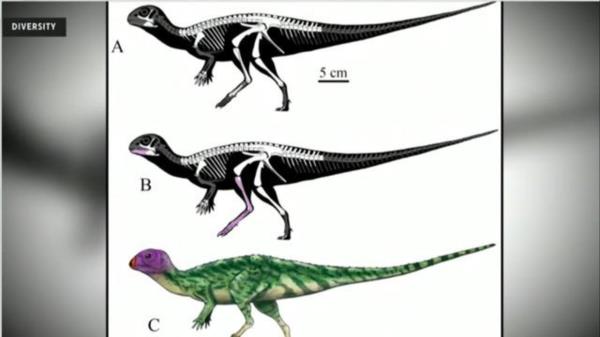我床头柜抽屉里放着一个琥珀色的玻璃镇纸。它曾经属于我的父亲,他最近去世了,在他之前是他的祖母。它的形状像一个立方体,两边都画着精致的花朵,在我的手掌里很重。但我很少把它捡起来,因为我没有需要称重的文件。这个对象占用了宝贵的空间,这些空间本来可以用来放书、纸巾或其他我实际使用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仍然保留着它,还有其他一些你可能称之为“情感杂物”的东西——对我个人来说有意义但不切实际的东西:一盒旧生日贺卡,一个破损的贝壳,一张不复存在的咖啡馆的会员卡。
我正在重新考虑这些纪念品和其他许多东西,因为我试图在我与丈夫和蹒跚学步的孩子合住的小公寓里腾出空间。但我似乎不能放弃它们。所以他们在房间的角落里收集,让人想起旧货店的随机性——而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精心策划的。我不一定喜欢家里的角落和缝隙里堆满了不匹配的垃圾,但这种杂乱满足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总的来说,它代表了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亲人的生活,现在是我不到两岁的女儿的生活。它将我与那些原本会感到失落的人和时代联系在一起。
在我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金属盒子,里面装着旅行时的火车票和博物馆通行证,感觉是那么遥远,就好像我在书中读到过一样。床底下有一堆旧衣服,包括我21岁生日时穿的那件有褶边的上衣。我已经有十多年没穿过它了,但当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我的手指仍然停留在廉价的褶边上;他们回忆起一个更自由的自我,如果更漫无目的的话。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12个不同的公寓里拖着这些设备。即使我重新开始,我也会想起以前的自己。
阅读:早期KonMari收养者的家现在是什么样子?

还有更多的人住在我十几岁的卧室里,我妈妈让我整理了将近二十年。偶尔,我也会勇敢地把旧俱乐部的t恤送到Goodwill,但一想到要和朋友们的家庭作业和笔记分开,我就感到奇怪的疲惫。我怎么会和这个二十年未见的女孩如此亲近,以至于她给我写了一张热情洋溢的便条,还给我做了一张个性化的拼贴画?我怎么还能和其他人做朋友?我被这些记忆迷住了,但也被一种苦乐参半的感觉所淹没。
其他物品是对我失去的人的小小敬意。去年上半年,我的父亲,我丈夫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因无关的原因去世了。从那以后,他们的东西慢慢地来到了我们家。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它们。所以现在,我丈夫的父亲在我们婚礼上穿的礼服鞋占据了我们衣柜的空间。我丈夫打算把它们捐出去,但还没有。有时,看到他们会让我猝不及防,我想知道他们是在帮助我们愈合伤口,还是在阻止我们继续前进。
在我们的空间里塞满过去的痛苦纪念品似乎是错误的。但根据哥伦比亚大学长期悲伤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研究科学家娜塔莉亚·斯克里茨卡娅(Natalia Skritskaya)的说法,坚持持有带有复杂感情的物品是很自然的。“我们是复杂的生物,”她告诉我。当我回想起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光时,它们并非完全没有悲伤;悲伤和失望常常徘徊在快乐和归属感的附近,赋予后者更多的分量。我希望我的家能反映出这种细微差别。当然,Skritskaya说,在某些情况下,执着于旧物品会让人无法接受损失。但避免所有悲伤的联想也不是解决办法。不仅清除我们空间中所有悲伤的迹象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且如果每个房间都被洗去了所有的痛苦,它也会被洗去它的深度。

阅读:近藤麻理惠和杂乱的特权
决定什么要留,什么要丢是一个持续的,直觉的过程,永远不会感觉完全完成或确定。“刚刚好”和“太多”之间的界限可能会波动,即使是我画的。我的心情稍有变化,一件珍贵的传家宝就会在一秒钟内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当我疯狂地寻找我的钥匙或一些重要的邮件时,这种感觉最强烈。这样的时刻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混乱的,我对周围的环境缺乏控制(因为我的许多东西都是被赋予的,而不是故意选择的)。然而,随着我们的孩子收到玩具,我们获得更多的装备,更多的东西进入了我们有限的空间。我偶尔也会卖掉一些我的私房钱。即便如此,我相信比任何专业组织者推荐的都要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是一个私人博物馆。某些物品可能将我们与更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祖父泛黄的行李牌不仅代表了他晚年选择的旅行,也代表了他早年被迫的旅行;二战期间,作为一名日裔美国青少年,他被转移到一个拘留营。另一些则只对那些了解对象用户的人有意义。我想起女儿画的第一幅“画”,差点把我和丈夫都哭了。这只是几个点,但她选择把它们放在哪里的想法奇怪地感人,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创造性自由裁量权的脆弱性。它还挂在我们的冰箱上。这些文物向我们家园的居民致敬,并纪念那些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人。
在我最后一次去父亲家看望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把他小时候家里的古董木制高脚椅。我父亲斜倚在床上,看上去比平时高,一想到他曾经坐在这把小椅子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们把它带回家给我女儿吃,她刚刚开始吃固体食物。几天后,我爸爸走了。那把高椅子还在那儿。
我的大多数亲戚,包括我父亲,都没有过着特别精彩的生活。他们的名字不会刻在建筑物上,也不会附在奖学金上。只有少数人还会想起它们,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们的私人物品还在,上面写着:有人来过这里。当我开始一天的生活,叠衣服,或者思考需要做什么时,我的杂物让我想起了那些充满我生活的人,现在,还有我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