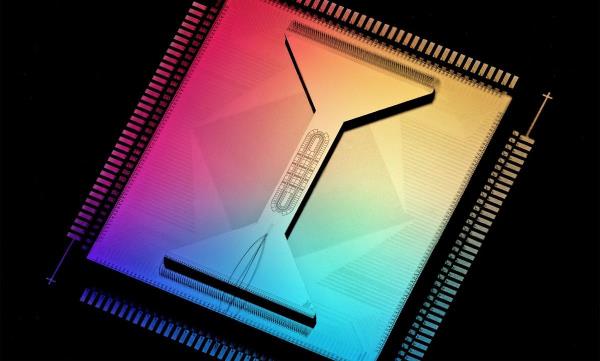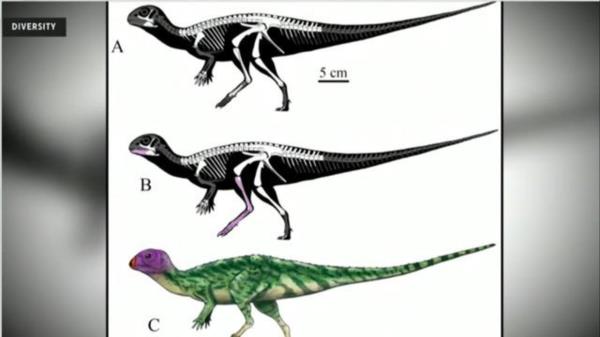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以来,可卡因流行病已经成为传说,我们离它的高度越远,它在集体想象中的影响力就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记忆本身的产物,但这也是对疫情的记忆被优先考虑的结果。
30多年来,执法官员、政治家和权威人士的说法一直主导着人们的谈话。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未以个人方式接触过这种流行病,除了他们在工作中所做的、在新闻中看到的或路过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快克毒品的流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80年代和90年代所有坏事的缩影——贫穷、犯罪、帮派、暴力,以及民权运动后美国贫民区所代表的一切。
但对于那些与可卡因疫情面对面的社区成员来说,它就像血肉之躯一样真实。毒品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来说,可卡因流行不仅仅是一篇文章或演讲中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集合。它植根于我们的社区和家庭。它发生在一些人的童年,不断被创伤、悲剧、威胁和压力打断。

米歇尔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不过我几乎没见过她。事实上,我不记得曾经见过米歇尔,但我被教导要害怕她。我的母亲是一个谨慎的女人,平时避免八卦,她会用长长的白色电话线把家里的电话从一个房间拖到另一个房间,和她的朋友们长篇大论地谈论《来自街头的米歇尔》。
有太多陌生人进进出出她的房子。邻居们整夜都能听到她的聚会声。她看起来“一团糟”。这一切“太悲伤了”,我妈妈会慢慢地摇着头说。她会继续谈其他话题,但我一直盯着米歇尔,努力想象几英尺外可能发生的事情。
阅读:“可卡因婴儿”恐慌揭示了阿片类药物的流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姐姐正坐在我家前廊上,一辆面包车停在米歇尔家门前。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妹妹什么都知道,我问她那些陌生人是谁。“咄!那是米歇尔的家人,”她补充说,那个小女孩是米歇尔的女儿。“她为什么不和她妈妈住在一起?”我问。我妹妹生气地耸了耸肩,好像这是她永远不会问的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回答说:“我不知道。可能因为米歇尔是个瘾君子。”
那是在1993或1994年。我当时只有五六岁,但听过无数次“瘾君子”这个词,通常是从其他孩子那里听到的。Crackhead是一个常用的侮辱词——某某人“表现得像个瘾君子”;“yo mama”是“瘾君子”。
我想,它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属于成年人的世界,使用它让我们觉得自己长大了。我想,我们之所以把“瘾君子”当作一个贬义词,是因为我们害怕它所代表的东西,那是我们任何人都可能陷入的谷底。当孩子们想要控制让他们害怕的东西时,他们就会这样做:他们把这些东西简化成单词,一口大小的东西,可以随时吐出来。
我无法理解米歇尔是个瘾君子。毕竟她就住在这条街上,而且她有自己的家庭。瘾君子被认为是来自某个地狱的外国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乞讨钱,否则就会扰乱社区生活。然后他们应该回到他们来自的地方——小巷,下水道,我们把垃圾扔出去的地方。
米歇尔在她所谓的女儿来拜访后不久就从附近消失了。她很快就被生活在我们贫穷的黑人社区边缘的其他人所取代。我有时会在街尾的便利店附近看到一个皮肤白皙的瘦弱女人。艾尔是这家店的老板和经营者,他称这个女人为“百里茜小姐”。
有一个人,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街上走来走去,总是匆匆忙忙,总是卖东西——夏天卖几袋散架的烟花,冬天卖崭新的羽绒服。和米歇尔一样,我认识的大人们也只是顺道跟他和百里茜说话。我计算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也是“瘾君子”。
我想,对于许多像我这样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毒品泛滥中长大的穷人和黑人孩子来说,这种微积分是很常见的。我们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最好不要去问。我母亲有个原则:管好你自己的事。当她撞见我偷偷地看街角的大男孩时,她也会这么说:“少管闲事。”就像在一个没有人谈论钢铁的钢铁小镇长大一样。
我调查了我的社区,看到了到处都是可卡因的破坏和残留物。我从我们社区的治安方式中看到了可卡因的影响,就好像在我们身上撒下了一张拉网。警察似乎不会满意,直到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被拦下、盘问、搜查毒品和武器、拘留、罚款、逮捕、监禁、不方便、半夜被叫醒、被羞辱。有些人最终会被殴打、枪击或杀害,但我们所有人都会被这种毒品时代的警察制度所感动。
山姆·奎诺内斯:美国治疗成瘾的方法已经偏离了轨道
学校就像是街道的延伸。在那里,是老师,主要是白人,对学生进行侧写。他们给我的同学贴上了“情绪不安”或“过度活跃”的标签,诊断他们有学习障碍,并据此解雇了他们。对于我们这些男孩,黑人男孩来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活力。我们说不出它的名字,但我们意识到了这种蔑视,并对此感到愤怒。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一头野兽的肚子里,它把不听话的黑人男孩整个吃掉,它把我们的反抗贴上不听话的标签,以此为自己辩护。
我不认为我的同龄人理解当时可卡因流行对我们年轻人的影响。我当然没有。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克服裂缝的阴影。它威胁着要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我们尽力逃脱了。我们避开了警察,他们把我们定性为毒贩和帮派成员。
可卡因的流行结束了,我通过努力、运气、母亲的养育和上帝的恩典熬过了它的余波。我们离可卡因时代越远,对可卡因的恐慌就越被对恐怖主义和其他21世纪美国危机的恐慌所取代。
大多数美国人对可卡因的了解都是以神话、刻板印象和含沙射影的形式出现的。当现在提到可卡因流行时,它通常是一个妙语。可卡因是一种超级毒品,毒贩是超级捕食者,不可救药的瘾君子和可卡因婴儿都被唤起来证明一个观点。或者它们被引用为20世纪后期的时尚,比如王朝、垫肩和酸洗牛仔裤。
当然,快克流行还有其他常见的用途。政客们像挥舞盾牌一样挥舞它,以转移和恐吓。在演讲中,他们援引我们国家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作为维持我们刑事司法体系的论据。或者他们用它来证明他们在一些与黑人生死有关的糟糕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想要答案。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记忆与我们从流行文化中所学到的关于可卡因时代的东西调和起来。我们正在把碎片拼凑成真实的历史。
通过数百次采访和多年的研究,我了解到的是,裂缝真正做的是暴露社会的每一个弱点。由贫穷和无能引起的不满导致了一代年轻人滥用毒品的猖獗,这些人正好从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契约的漏洞中掉了出来。可卡因的流行暴露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脆弱的群体是多么脆弱,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是多么不关心他们,人们是多么宁愿让自己的美国同胞消失,也不愿帮助他们。裂缝将社会最糟糕的本能——贪婪、恐惧、羞耻——集合起来作为回应。
阅读:白人吸毒者如何使海洛因成为公共卫生问题
但我也了解到,即使是像可卡因这样强大的物质,也无法与黑人一心想让彼此和他们的社区活下去的韧性相提并论。
我经常想起《街尾》里的米歇尔,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我喜欢想象她离开这个社区是为了治疗。她戒了毒,和女儿一起搬进了一所大房子,她女儿都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不在一起了。
然而,多年来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报道告诉我,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出现。更有可能的是米歇尔被逮捕并被系统吞噬了。如果她今天还活着,而且干净,她可能会带着流行病的残余生活——犯罪记录、慢性疾病、创伤、内疚、羞耻。
为了她和其他许多人的利益,我们应该把可卡因的流行与历史的其他部分调和起来。为了向前迈进,我们必须以诚实和同情的态度面对可卡因流行的遗留问题。我们必须衡量它,赋予它意义,并将这种意义融入到我们是谁的故事中。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朝着治愈和正义的方向努力,确保过去的错误不再重演。

《当可卡因为王——一种被误解的毒品的民族历史》novan X. Ramsey